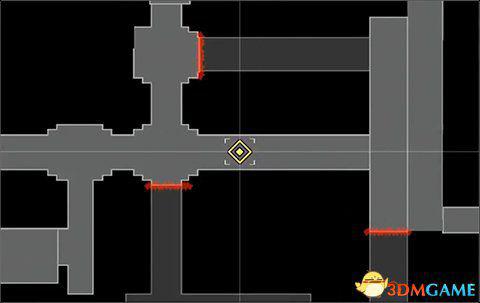短篇小说:难忘恩师 | 作者:靳明全
东京巢鸭,轻轨车站旁边一条狭窄的小路,一根电线杆下站着一位女子,远看,她像《白蛇传》的白娘子,浅白素装,身段苗条,亭亭玉立。
河泽告诉金泉:“她是妓女,你路过不要正面盯她脸,那样是邀约她。”
河泽说话十分轻松,金泉心里十分紧张,有生以来,只在书上见过妓女,身临其境,自然很不习惯。憋住气,走到妓女面前,好奇心驱使他禁不住瞧了瞧那女子,白净的脸,没有涂脂抹粉,嘴唇也非肉红。女子的眼睛闪闪发亮,碎步直奔金泉面前。
河泽大叫:“八格牙路!”
女子吓了一跳,慌忙转身,快步离去。
“你们政府不管她们吗?”金泉莫名惊诧。
“每季度要开展你们国家那样的扫黄活动。不过,这些人预先知道,早已躲起来,警察和记者们来到这些地方,转一圈,发一则消息:环境优良,不伤社会风化。扫黄活动一过,妓女的生意又活跃起来。给她们钱,她们给你乐。”大学讲师河泽谈起这些事,有声有色,嬉皮笑脸,津津乐道,一点没有像国内大学教师谈此类事的严肃。
金泉想,这是日本学者的德性吧。
一路谈笑风生的河泽把金泉领到硕士导师原田教授的研究室。他朝门轻轻敲了三下,然后笔直站立在门前,低着头,憋住气,犹如进入北京伟人纪念堂,神色无比严肃,肃穆,敬畏,与刚才谈妓女的轻浮貌大相径庭。
原田教授亲切招呼金泉坐在研究室桌子的对面。河泽端茶倒水,然后笔直地站在原田教授身后,聆听导师与金泉的随意谈话,不喘大气。
师道尊严的气氛浓浓罩着研究室。金泉有些后悔:自己在导师孙克恒、支克坚的生前,没有表现出像河泽对导师的敬畏。导师与同行交流学术,他没有端茶倒水,更没有笔直站在导师身后,大气不喘地聆听他们讲话。
孙克恒教授,山东人,5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,分配到兰州大学,后调西北师院任教。他两眼炯炯有神,五官端正,脸色黝黑,肩宽腰细,身材匀称,无论长相与身段,极像电影《从奴隶到将军》的演员杨在葆。
一日,孙教授把金泉叫到他家书房,泡了一杯茶,说:“你在《天府新论》发表的论文我看了,包括你在《重庆社会科学》的论文,我认为,最大的毛病是论述不深刻。就像你当秘书行文差不多,材料堆积,然后分类,最后归纳几点作为结论。这种方法写出学术论文很平庸。要写好学术论文,应该抓住一个要点,紧紧围绕论题,像剥笋子一样,一层一层地深入,最后得出结论,有自己的创新点,不流于平庸。”
时值秋末,孙教授的书房窗户关闭,没开暖气。穿着棉衣听着导师说话,金泉的额头冒出了汗珠,头犹如啄米的小鸡,不停地点,因为,做学问的缺欠被导师切中要害,
这时,师母进来了。师母是西北师院附中的语文教师,江南女子的白净脸色,樱桃小嘴,说话声音洪亮:“老孙,你马上去粮店把米拿回来。”
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,当地政府每月给他们配备一些精细米。在兰州,一般人凭粮票只能按定额配购面粉和粗糙的大米。 夫人一声呼唤,孙教授站起来,点头,仿佛士兵听连长的指令,大声回答:“好!”
金泉急切地站起,说:“孙老师,我去给你领大米。”
师母没说话。孙教授见金泉的执着劲,就说:“好吧,我俩一起去。”
兰州寒风凌冽,刺入颈子,老师和学生不禁打寒颤。走在大路上,孙老师咳嗽几声,谈话显得特别的知心。他称自己是外来户,当地最大的势力是兰大系。兰大历年的毕业生把持省市部门的要津。在甘肃,北大毕业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授只有两人,另一位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吴小美,是他的师姐,因为是《中国现代文学丛刊》编委,她的学术地位较高。自己呢?当上教研室主任,还是支老师担任了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后转让他的。他对支老师有些微言。支老师属兰大系,与孙老师齐名硕导,在西北师院招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生,硕士学位由兰州大学授予。
听了孙老师的内心话,金泉明白导师之间的微妙关系。作为学生,他绝不能掺和进去,说东道西,只是轻声地哼哼。
孙老师夫妻间也有不尽人意之处,金泉凭直觉,师母对孙老师有些“女权”。作为学生,他更不能选边站。不露感情,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。
读研进入第三学年。金泉赶前不赶后,把学位论文初稿交给孙教授,很快有点后悔。这时,孙教授咳嗽比较严重,经常在西北师院医院吊药水。在吊药水之际,他仔细审阅金泉的初稿。寒假将至,孙教授住进了医院。在病床上,他把论文初稿交给了金泉,上面用红笔写了批示和修订意见,密密麻麻。
看到孙教授因咳嗽而声音沙哑,眼仁发黄,眼神迟滞的病状,金泉满脸通红,真想待在病床前,为他端屎倒尿,以报师恩。
寒假至,金泉赶回重庆。临行前,他买了一大篮水果放在病床旁边,给声音沙哑的孙教授说:“孙老师,多多保重。”寒假快结束,金泉闻孙教授患肝癌,已是晚期。他立即起身赶到成都。这段时期,四川农民去新疆干活的很多,西行火车,一票难求。金泉在成都耽搁三天才成行。回到西北师院得知,三天前孙教授病逝。临终前吴小美教授看望他。孙教授用全身最大的劲说清楚这句话:“研究生的学位,拜托了。”
闻讯,金泉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在孙老师的书房,见到他的遗像,扑通跪在地上,嚎啕大哭。站在旁边的师母,眼泪汪汪,不能自已。两人的悲号荡出窗外,直上云霄,迎合起孙教授临终前沙哑的声音。
一日,金泉去现代文学教研室陶副教授家交作业,遇上高校教师之间缺乏人情味的一幕。
脸色白净的陶副教授,黑起脸当着金泉面大骂孙夫人,说她对孙教授不好,像泼妇,让孙53岁就逝世。骂完,他的话锋一转,说孙教授生前住学院分的教授屋,三室一厅,他住两室一厅。如今,孙夫人没资格住教授屋,自己马上要评教授,他要向学校反映,与孙夫人交换房屋。
金泉这才明白,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。陶副教授像泼妇般骂师母的真正意图是换房。这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私利,不像工人农民那样赤裸裸地争闹,而是采用铺垫手段,强词夺理,以达到无人情缺人性的个人目的。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之一就是少人情乏人性。诚然,目前高校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不理想,可是,孙教授尸骨未寒,不管怎么说,换房不符合情理。金泉急忙说:“老红军的高级住宅,在他死后,妻子不是老红军,也应该继续住,直到死后退房。”
陶副教授鼓起眼睛,振振有词:“孙教授不是老红军。我住教授屋,要带硕士生。你师母只是普通中学教师,她能为师院做这么大的贡献吗?”
想到自己的作业要靠他打及格分,才能拿学位,虽然瞧不起他,但不敢极力争辩,一言不语,心里却愤愤不已。高校丑陋的知识分子,追逐个人利益,无人情味可谈。金泉默默地离开了说话激动的腮发抖的陶副教授。觉得他那白净的脸变成丑陋的花脸,孙教授黝黑的脸是多么的慈祥可亲,反差如此大。念及导师的恩情,金泉决定:为了正义,为了人的尊严,为了保护师母的合法权利,如果陶副教授把换房企图付诸于行动,即使自己不要学位,也要与他抗争。
事情发展并非陶副教授的一厢情愿。毕业离校时,金泉向师母告别,师母依然住在教授屋。
导师支克坚是浙江人,57年兰州大学毕业,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闪烁在西北上空的一颗新星。不到50岁,担任了《中国现代文学丛刊》的编委,成为该领域顶尖级学者之一。他在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学评论丛刊》《中国现代文学丛刊》《鲁迅研究》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影响极大的论文。其中,关于阿Q革命说,一反昔日权威学者说法,在学界提出,阿Q是愚昧的流氓农民形象,阿Q革命是他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形式,阿Q希望成为压迫者,企图用革命来改变被压迫的身份。支老师的文章,反驳当时学界主流说即阿Q无产者革命说,立即引起了学者的极力关注和争鸣。
金泉曾冒出过跟支教授读研的想法,但有自知之明,仰望知名学者而却步。他万万没有料到,考研材料转到西北师院,拜在支教授的门下。
充溢敬畏之心,金泉初次遇见支教授有点儿失望。支教授身材矮胖,大头,宽脸,深度的眼镜片里眼珠直转,长相有点像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里的日军翻译官。与西装革履的孙教授穿着有别,他那不合身的衣服外包经常鼓鼓的,仿佛里面装了没有吃完的大面包。更深的印象是,支教授初见金泉,眼睛竟然朝着地面,有点儿腼腆,而学生正在仰视他。然而,支教授给五位研究生及一位访问学者开讲,犹如磁铁吸住铁粉,学生听得如痴如迷,尿胀了都不愿意去厕所。
支教授上中国现代文学专题课时讲到,王瑶在一次学术会上告诉他,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,一群知名学者在北京一个高级宾馆的会议室,商量召开全国性的茅盾研究会议事。突然,会议室门被撞开,一个老太太冲进来,咬牙切齿大骂王瑶等人:“你们这些学者,研究什么茅盾?你们知道吗?我给她打过胎。”
学者们大吃一惊,但不便撵老太太出去,因为,她是全国政协委员、老革命、老党员秦德君。
后来,金泉查阅了许多资料,才知道:茅盾1928年流亡日本,与秦德君同居,茅盾夫人孔德沚闻讯,在上海要跳黄浦江。
支教授讲完课,总要留时间叫研究生们讨论,畅所欲言,各抒己见。下课前的一刻钟,他进行总结。一次,他说出了金泉做学问终身难忘的话:“你们学习讨论,如果产生了独特的想法,冒出思想的闪光点,一定赶紧用文字留存,写出草稿。然后,想法寻觅有关资料,思考它的合理性,进而形成文章的初稿。再后,不断打磨、修订、完善,形成有新意的定稿,争取问世,以求读者反映和社会效应。这样做学问,比那些铺陈归纳大家都表达过的观点强得多。”
支教授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,虽然谈不上篇篇是珠玉,但是,他那几篇学术价值极高的论文,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。
受教于支教授, 金泉把茅盾流亡日本的消极绝望情绪与秦德君的恩怨联系起来,形成了一篇茅盾研究的论文草稿,尔后写出初稿,最后定稿为《论茅盾流亡日本时期的消极绝望情绪》,刊登在《贵州大学学报》。在一次茅盾研究学术研讨会上,他就此论文作了发言。一位茅盾研究著名教授,极力维护茅盾崇高无瑕形象,厉声驳斥金泉论文之不足。他的话一落,另一位茅盾著名专家站起来,反驳那位斥责金泉的教授。双方各带的研究生站在自己导师一边,纷纷发言,对峙争辩,会场的学术气氛很热闹。
金泉明白,他那篇论文在会议上引起的只是口水仗,与文章争鸣有别。但是,比那些引不起读者注意的平庸论文好。踏上学术路,金泉基本朝着支教授指出的方向走。思考问题,突显了闪光点,及时用文字形成草稿,日积月累,草稿堆积成山。然后,从“山”里发掘出初稿。初稿日益增加,进而做到资料翔实,思考缜密,完成定稿,争取有一定质量的论文源源不断地发表。
支教授属于两栖学者,他担任过甘肃省文联党组副书记、社科院院长,这引起同教研室同龄的洪副教授极大不满。洪副教授说话妹声妹气,音量小,怨气足。他的教学科研水平一般,学术实力达不到教授,心里始终不服已评聘的教授;组织能力达不到科、处职务要求,却瞧不起教研室主任及系主任。他最大特点是,作为无所长进、或长进不大的弱者,却对同行的强者发怨气,滔滔不绝。洪副教授对金泉说:“你们支老师,不应该脚踏两只船。在文联社科院当领导,就不要占我们西北师院教授硕导的名额。做师院的教授硕导,就该放弃社会上的行政职务。”
洪副教授8年前评上副教授,没有发奋,没有再接再厉,只是对教授职称、副系主任职务,望断秋水。他的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远不及支教授,他的怨不过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嫉恨。倘若与支教授比试学识和能力,他不过是站在重庆的涂山,要与喜马拉雅山试比高,只能自寻烦恼。学术地位靠实力,组织办事靠能力,不在一个等量级别上,喋喋不休比高低,实乃学术仕途之大忌。
湘西师院应届本科生王建考研初战告捷,就读西北师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。他绰号黑鼻子,入学很自卑。因为,鼻尖长了一颗豌豆大的黑痣,苦于无女朋友的关爱,常常独自待在寝室,对准手中的小镜子看鼻尖的黑痣有无变化。许多硕士生花大量时间看书,他花大量时间看鼻子,自然学业长进不大,课堂上讨论只能说出平庸的话,难免老师和同学对他小觑。鼻子的自卑添上学业自卑,倘若把自卑换成励志,弱势也能成为强势。黑鼻子可不这么想。那时,硕士生严进宽出,他保持本科生考研的水平,多看鼻子少看书,不愁拿不到学位。所以,得过且过的想法代替了励志的决心。
在黑鼻子面前,金泉存在自卑感。黑鼻子是正式硕士生,拿到学位可以自由选择地区和高校。自己已卖身,口袋有卖身契,毕业要被甘水师专死死卡住,动弹不得,选择地区选择高校是幻想。时值正式硕士生小觑代培生的现象突出,这加重了金泉心里隐痛。不过,金泉可不是黑鼻子。身处逆境,他的励志信念萌生,时常考虑如何改变自卑的代培生地位。
通过交心谈心,孙教授理解同情金泉的处境,他知心地说:“甘肃本土的势力大,甘水师专也如此。你作为外来户,在那里学术很快发展,难。如果你能找到重庆地区的高校代培就好了。不过,重庆发展快,培养硕士生的高校多,要那里的高校出钱代培,比较困难。”他眉头紧锁,露出有点后悔的样子,接着说:“你复试时,我动了一个念头,录取你为正式生。考虑到本专业已招了4名正式生,也就算了。那时候我俩不熟悉呢。”
听到这话,金泉身体发热,深深地感动。有了导师的认可,他心里盘算:如何寻觅挪动的代培单位。联系了重庆一些院校,正如孙教授所言,不能如愿。他把请求代培单位转向重庆相邻的云南和贵州,发出10封信,一个月后收到1封回信。绝望的心冒出一线希望。
黔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较弱,希望该专业的硕士来任教,虽然省上拨下专款,但没有联系上硕士生。系主任徐龙的回信谈及,如果金泉能说通目前的代培单位,他们愿意还代培费,接收他为代培生,获学位后在黔大最少工作八年。
接徐主任信不久,金泉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看到一则小消息:徐龙的儿子患肾病,需要换肾,钱资不济,同事们发起了募捐。徐龙的学生、知名作家黄世光豪爽地捐款1000元。金泉性格豪爽,感恩徐龙回信,立即勒紧裤腰带按募捐地址汇去200元。然而,徐龙儿子病情迅速恶化,还没募捐到换肾款的一半,病逝。徐龙退还了所有捐款。金泉收到汇去的200元。此事留给徐龙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
转代培关键要甘水师专放行。甘水师专校长王运山,瘦高个,曾任西北师院历史系副系主任,57年被错划右派,送去劳改农场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平反。靠同时平反现为省教育厅领导的提携,他来甘水师专任现职。
一日,金泉专程从兰州乘火车到了甘水市,午饭后直奔王校长家。
王校长热情地招呼他坐在客厅。金泉哭丧脸,诉说家庭的种种困难,然后直奔主题。得知金泉要跳槽,改为黔大代培,王校长脸色骤变,像李逵一样黑起脸,断然道:“想跳槽,没商量。你拿出代培费一万五,加上罚款,现金三万,我才能考虑放不放人。”
听到王校长如此刻薄毫无商量余地的话,金泉怒从心生,禁不住冲出一句话:“我读书前是国家干部,你说话的口气,好像我是犯了罪的人。”
王校长昔日被“国家干部”整过,他什么话都可以原谅,就是不能原谅说这种话。脸气得成为猪肝色,三角眼冒出熊熊烈火,鼻翼抖动,一下子站起来,大声斥道:“走!有话到学校办公室去说。这是我家。”他的手用力朝门口一挥,犹如一把尖刀,挥进金泉的胸口,鲜血浸透衣裳,剧痛难忍。脑瓜出现一片空白,漠然站起来,没有知觉,没有痛苦,没有烦恼地走出王校长的家门。
身后传来猛烈的关门声,差点把他的心脏震落下地。
人世间存在这种人,被整的时候窝气,一旦他有机会整人,非常凶狠。三天后,王校长和师资科杨科长去兰州开会。会间,他带杨科长找到昔日同事现西北师院的秦院长,说明:金泉这种人不值得培养,希望秦院长支持甘水师专的要求。
听完王校长述说,秦院长的两腮肌肉在抖动,断然回答:“你们学校打一个正式报告,我签字,马上让他退学。”
杨科长在西北师院读书的同学杨月惠,甘肃民院讲师,作为支教授的访问学者,她和金泉同桌听课,此时与杨科长同在会场。闲聊中,杨月惠谈及支教授的得意门生金泉。杨科长把王校长与秦院长的对话告诉了她。会后杨月惠把消息告诉了金泉。
金泉呆呆地望着杨月惠,伤心不已,眼神不是感激,也不是痛心,而是对于一种无法避免又势不可当的压力产生的紧张。他的身子瑟瑟颤抖,这与其说是由于一阵冷风,不如说是由于杨月惠的话使他心中极其恐怖。恐怖产生怨恨,怨恨简直要丧失理性。如果他手中有枪,面对王运山一定会扣动扳机。不久,他趋于冷静,立即想到了导师支克坚。
支教授在家里冷静地听完眼眶发红的金泉的诉说,非常果断地做出决定。他给甘水师专白副校长通了长话。白副校长是国内敦煌学知名学者,也是支教授为副组长的省高级职称评委会的一名评委。支教授告知:金泉在西北师院读书,尊敬师长,团结同学,努力学习,读研期间发表了有质量的论文,不能因为找到一个代培单位,提出自己的申请,就勒令退学。
第二天,支教授专程找到他的学生现西北师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赵副院长,讲出了与白副校长所讲的话。尊师的赵副院长对支教授点头称是。
遵从支教授所嘱,金泉奔赴甘水,找到白副校长的家,他把兰州到贵阳来往的火车票拿出来,说明联系转代培单位之艰辛。火车票整齐重叠,高度约两寸,这足以让白副校长为之动容。他忍不住发出“啊”地一声,心里的反应是怜悯。支教授的电话加上这个细节,为挽救金泉免于挫败起到关键的作用。
在甘水师专校长会议上,王校长提出,为了不让代培生跳槽事蔓延,杀一儆百,以儆效尤,甘水师专应该中断金泉的代培资助,西北师院令其退学。
他的话说完,白副校长立即谈了他的意见:“如果金泉退学,回到师专怎么安排呢?不仅仅是浪费已支出的代培费,师专还背上一个不能用的包袱。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我看,不能因为这位年轻人申请转代培就断送他的前程。还是说服他收回申请,继续完成学业,按协议来师专服务八年再说。如果,他能让黔大交换一位来师专工作的硕士生,放他一把,也何尝不可?”
白副校长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领导的赞同,王校长只得作罢,金泉被勒令退学的危机消失。但是,挪动代培单位的困难,难于上青天。好不容易考上黔大的正式硕士生,谁愿意转为小小的甘水师专代培呢?如果考上的是代培生,又怎么愿意挪动到小小的甘水市?
甘水师专校长会议的决定,显然,留给金泉的只有一条活路,就是在那里工作八年,与王校长关系又是如此的槽糕,苦闷的金泉,几个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,彻夜不眠,眼睛闪动流不出的泪。然而,坚韧的性格促使他又自费从兰州奔赴贵阳,除了咬牙硬闯,别无选择!
徐龙主任对交换代培生无可奈何。今年起,徐龙和另一位副教授开始在黔大招不授学位的硕士生,(完成学业者申请有学位点的高校授学位。)考进来的研究生有选择地区、选择高校的自由。
金泉提出,如果他动员愿意毕业去甘水师专工作的考生,考上了黔大,和自己交换,可以吗?
徐龙认为,有这样的生源他当然支持,何况,黔大本专业首次招研究生,生源还是一个大问题呢。韩信点兵,多多益善嘛。金泉进而寻问考研的要点。徐龙主任谨慎地说出一本教材的有关章节,还讲了他和另一位副教授近年发表的几篇论文。
金泉返回西北师院,苦苦思索了几个晚上,决定:给比甘肃省更偏僻的地区青海、宁夏、新疆所在院校中文系应届毕业班,以及甘肃省内一些师专的中文系应届毕业班(考生为同等学力者)去信,收信人为班长,托他(她)转告全班同学:金泉受委托,凡是报考黔大中文系的考生,获取学位,在甘水师专工作的,黔大可以优先录取。并且,金泉可以告知考试的要点等等。
20封信发出。西北师院大多数同学认为,这是异想天开,根本不可能实现。还有人认为,金泉自诩招生老板,在招摇撞骗。个别同学认为,金泉发这些信有创意,即使不成功,而拼搏精神殊为可贵。金泉心里明白,死马在当活马医,尽了人事,只待天意了。
出乎所有知晓此事的同学意料的是,不久,金泉收到4封回信,写信者全是中文系应届生。1封信来自青海师院,3封来自甘肃省三个师专。他(她)们都迫切希望考上黔大,毕业后在甘水师专任教是他(她)们的理想。金泉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,他根据自己的考研经验和了解的情况,一一回信,把黔大考研的要点详细告知。同时,4位考生的姓名告诉徐龙主任,渴望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,甘肃省内比甘水更偏僻的师专一位考生成绩上了复试线。
从徐龙主任那里得知,录取她已成默契。趁热打铁,金泉立马奔到甘水师专白副校长家。白副校长万万没有料到,当时他是想不让金泉退学,为此而提出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交换方式,如今竟然成为了现实。他为金泉的毅力而动容,作为一名著名学者,心里佩服坚忍不拔的学生,决不食言,就极力促成了甘水师专与黔大交换硕士代培生事。
甘水师专宋副校长带杨科长作为公差来到了黔大,当事者金泉自费随往。在黔大附近的花溪公证处,办了甘水师专,黔大,金泉三方签字的协议。金泉毕业到黔大工作,尔后三年,每年来甘水师专无偿授一学期课。考取黔大的那位考生,三年后毕业获取学位,即赴甘水师专工作。签了协议,金泉长舒一口气,五味杂陈,感慨万千,独自对天长吁:天意啊!天意!
金泉到黔大报道的第二学期,到甘水师专上课,时值八九年“6.4事件”发生,学校动荡不已,师专的领导换了不少。金泉回到黔大,再未去甘水师专。三年后,就读黔大那位硕士生取得学位,不愿意去甘水师专工作。那时,硕士生不如三年前之稀缺,黔大支付甘水师专代培费1.5万元则了事。这是后话。
金泉获取兰大授予的硕士学位,离开西北师院时遇上一个大问题。他拿着三方协议书找到西北师院研究生处于处长,取得他的同意,培养科任科长在金泉派遣证明上写明:贵阳市,黔大。任科长对金泉说:“凭这个证明,你去省教育厅换成正式派遣证。你的学籍档案里写明甘肃省内报道,现在去外省,省上很难认可啊。”
如果真如任科长所言,金泉转代培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,前功尽弃。没有甘肃省的派遣证,他在贵阳上不了户口,在黔大无法报到领工资。老天保佑啊!老天保佑啊!金泉心动过速地朝甘肃省教育厅直奔。
骄阳对于兰州年轻女人而言是多么的可贵,一年中只有几天炎炎夏日,年轻美貌的女人像过盛节一样,穿起五颜六色的连衣裙、短裙,犹如翩翩起舞的花蝴蝶,在闹市花枝招展,一展风姿。金泉来到教育厅大楼,见不到蝴蝶般的女人,因为,这里离闹市较远。
教育厅大门内外判若两景,门外冷冷清清,里面闹闹嚷嚷。一楼大厅坐着的站起的人,抽烟吐雾,一片唠唠叨叨话语。电梯门口等候一群人,闹嚷声,细语声,侧耳不吭声,各取所需,此起彼伏,人群的共同目标是等电梯上行。办派遣证手续的办公室在11楼,一楼的电梯门一开,金泉赶紧挤入电梯内。进了派遣办公室,办公桌前许多人的眼睛刷地望住金泉,只见他气喘吁吁,脸色因过度紧张显得十分苍白,嘴角边冒出白沫,说不出话来。办公室一人好不容易明白了金泉要办的事,他非常同情地说:“快!快上12楼,吴处长可能还没有离开。”
拿到吴处长签字的纸条,金泉真想给他跪下谢恩。他必须控制万分激动,去办理正式派遣证。跑进下行的电梯,稀里糊涂地到了1楼。出了电梯门,忽然想起办派遣证办公室在11楼,急忙回电梯,电梯门一下关闭,红色箭头是上行。金泉在门外急得捶胸顿足,现在是下班时间,电梯上行快,接各楼层下班的人下行很慢,他害怕派遣办公室关门上锁,急得脸色苍白如水,额头汗流满面。终于,乘电梯上了11楼,派遣办公室门开着,一个工作人员在等他。
“胜利了!胜利了!”金泉出教育厅大门,仰天放声大叫,差点儿把他的喉咙裂开。路旁行人稀少,一个壮汉用异样的警觉的眼光盯住他。一个穿着花色连衣裙的女人牵着五岁左右的女儿走。哇!——小女孩被金泉叫声吓得哭起来。年轻女人一边慌忙用手指抹女孩脸上的泪,一边劝:“别怕,别怕,叔叔病了。”
金泉乘坐成都火车的前一天,他去了孙教授家,当着师母的面,向导师的遗像深深地弯腰鞠躬。接着,他去支教授家,得知:支教授刚才乘车去了机场,赴北京开会。金泉去附近的花店购置一束鲜花,呈送给师母。花束上插了一张花边纸片,上面写:没齿不忘恩师情金泉 敬上 1988年7月6日
支教授到点退休,70岁定居儿子成都的家。那时,金泉每周授课穿梭于重庆与成都。因为妻儿住重庆,所以他往往到了成都上完课就返,与支教授在成都仅仅见过两次面。支教授给金泉表达“成都气候适合养老,但我朋故少”的遗憾。
一日,金泉正在给川大文新学院博士生上课,衣服包里的手机不停地震动,他打开手机,一位同门告知支教授逝世的噩耗。课一结束,金泉打的士到了灵堂。在支老师的遗像面前,饱含悲痛三鞠躬。这时,他十分后悔,为什么在支老师生前,没有常来他身边,接受教诲。支教授的学术根在甘肃,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,在成都离开人世前几年是多么的孤独寂寞。
悔意又一次涌上金泉心头。www.dushijiaoyu.com
免责声明:本文为转载,非本网原创内容,不代表本网观点。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,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、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,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
-
易烊千玺夜景随拍 四字真是妥妥文艺男啊
【易烊千玺夜景随拍, 四字真是妥妥文艺男啊】20日,易烊千玺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夜景随拍照。四字确实是妥妥文艺男青年啊。[详细] -
2023年第一季度5部高分剧,《狂飙》排在第三,你追过哪几部?
第五部《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》 豆瓣:7 8 主演:张若昀、王阳 剧情点评:一开始感觉有点无聊,但是后续渐入佳境。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邓知县和帅家...[详细] -
原创舞台剧《魔域·亚特之光》首演 共赴“爱与和平”成长征途
舞台剧《魔域·亚特之光》剧组 张帆 摄 中新网北京8月19日电 (记者 应妮)全新原创舞台剧《魔域·亚特之光》19日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[详细] -
众多电影人江西庐山推荐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
中新网庐山8月21日电 (记者 吴鹏泉 姜涛)第三届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主题盛典20日晚在江西庐山举行,众多电影人在活动中推荐中国影史经 [详细] -
直击义乌疫情:病毒隐匿性更强 一县支援一镇保供
发布会现场。 金华发布 供图 (抗击新冠肺炎)直击义乌疫情:病毒隐匿性更强 一县支援一镇保供 中新网金华8月14日电 (记者 张斌)8 [详细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