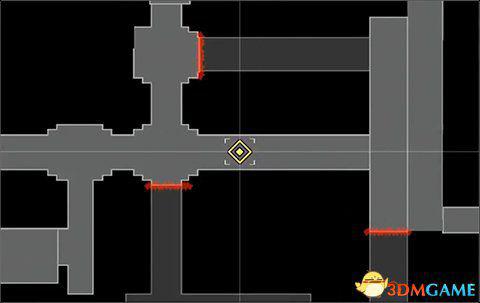甲乙:永远朝南的房子(中)
死神笼罩小镇
小镇上每天都有人饿死。呼啸的大北风以及寥远、惨白的雪野,更使得饥馑的人们孤苦无依。
我家隔壁住着一位瞎男人,平常很和善,出入总不声不响的,现在家人自顾不暇,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吃了,他受着饥饿的煎熬。某一天,他摸进我家的厨房,偷吃了母亲起早蒸熟的糠饼。
自此,他不好意思见人,也无力再走出家门。之后不久,他饿死了,一群同样饿得摇摇晃晃的人悄无声息地把他抬往墓地。
饥荒的尽头不知在哪里,父母忧心忡忡。四十五岁的父亲对故土的思念就在这时开始泛滥起来。回老家,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消除不了,关于故土的回想竟使得原本严厉异常的他变得有一些温情。他讲起老家的山,老家的田地,他说我们回到老家肯定不会饿死,因为那里一年到头都是绿的,最不济也有青菜可以充饥。
想来母亲一开始是随口附和过他的,大约并没把他说的当真,后来见父亲越来越急切,母亲变得警觉起来,于是断然正告父亲:真要走你自己走,我和孩子们是不会离开东北的。
在我的印象里,母亲这样公开违拗父亲意愿的事几乎没有过。她顺从父亲,很少和他争辩什么。
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,在家庭中事事说了算。他在家的时候,我们兄弟姐妹连大声说话也不敢,踮起脚走路,父亲午睡,讨厌惊扰,连苍蝇也不许飞,我们姐弟几个轮流拿蝇拍打苍蝇。
对于母亲来说,父亲那时的权威高于一切。但综观父母的一生,母亲由年轻时对父亲的顺从,到后来的不顺从,以及晚年的事事对立和不妥协,显示了人生很复杂的因素,这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。
父亲的强横也逐渐演化为晚年的病弱和无奈。可以说母亲敢于和父亲意见相左就是从这次开始的。父亲的打算使母亲产生一种远去异国它乡的恐惧。她还从未想过某一天要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小镇。
她知道一些女人离开小镇后的悲剧,如她很熟悉的一位女子,随丈夫去某个边远地方,吃了很多苦,几年后还是一个人回来了。
小镇上人尤其对南方没有好感,认为那里人奸滑,气候死热,北方人去了没个好。姥爷姥姥也反对女儿随女婿去南方。
初次去南方
父亲开始天天和母亲磨嘴皮子。父亲去意已决,但母亲仍然立场坚定。
有一天,一场暴雨之后,父亲去到山后的姥姥家,当着姥爷姥姥痛哭一场,竟一下感动了两位老人。他们松了口,母亲也不好再一口咬死。于是商量出个办法,就是让父亲带我和两个姐姐先到南方看一看,把情况搞清以后回来再说。
母亲不相信父亲回来以后会跟她如实地说老家的好与不好,所以一再嘱咐我把看到和听到的都记在心里,回来向她报告。
事实证明母亲的想法是天真印,因为我对事物还缺少分辨能力,再说父亲会把他的想法原原本本地灌输给我的。
那次去南方是我平生头一回出远门,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都很新鲜,如在南京的浦口,我们乘坐的火车给载到船上过江,火车随着行驶的船晃晃悠悠;俯瞰江面,浪花翻卷,江鸥飞翔。但在去安庆的大轮上,我弄出件大煞风景的事,使得旅行的快乐减少了许多。
事情的起因是我们从大虎山动身之前,吃了好久去除籽粒后的玉米芯子磨成的粉,拉不下屎,有时急得用手抠。父亲给我开了一些泻药,一次服一粒,起初并无效果,但在大轮上,饭食油水多些,泻药猛然见效了。夜晚我还在睡梦中,一股秽物从肛门中喷射而出,竟然滴到了下铺旅客的头上。
那是个采购员模样的人,叫苦不迭:这小鬼,要死,怎么搞的!
父亲连连给他道歉。解释了事情的起因,那人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父亲带领我们去的地方,并不是他在长江北岸的老家,而是江南小镇大渡口以东一个叫挖沟的小村庄。因为他唯一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在那里,可以去投靠一下。
也许是冬日天气的关系,挖沟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脏黑破败,低矮的茅屋没有什么生气。父亲的姐姐──我的大姑,是个衣服灰旧、脸腮凹陷的老太太,老是咳嗽吐痰,对我们也没显出什么热情。
她从小就到姓金的人家做童养媳,日子很苦,成婚后生了七个女儿,没生儿子。女儿早已都出嫁,老伴多年前去世了,现在她一个人住一间小屋,用一口小瓦灶,自己烧饭吃。由于通风不好,烧饭时屋里烟气呛人,天长日久,墙壁窗框都给熏得黑乎乎的。
现在挖沟居住的有我的二表姐、五表姐、六表姐。她们的年龄都和我父亲差不多,但依辈分还要喊我父亲“老母舅”。几个表姐夫也都是比较本份的农民,不大说话。他们对于父亲要带着一家人来挖沟落户,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
大姑的小屋里是呆不住人的,父亲就整天带着我到田间地头,看他所讲的“四季如春”,把一切绿的植物深刻地灌输到我脑海中去。
我想他这时已经定好计谋:把我的两个姐姐作为“人质”放在挖沟过年,不再带回东北了,以使得母亲有牵挂;而对我是每天进行“南方好”教育,让我背书一样念诵南方的咸鱼腊肉怎样香气四溢,地里青菜如何新鲜脆嫩,亲戚乡人怎样热情,弄得我头昏脑胀。父亲先是威胁,后是利诱。他决心让我成为一个围绕他指挥棒转的宣传员。
在父亲抱着必胜信心,率领我返回大虎山时,我的两个姐姐就给可怜兮兮地留在了挖沟。她们要呆上几个月,等我们全家过来才能会合。如果母亲仍然不愿过来,她们的处境就有些悲惨了。
当我回家见到母亲后,母亲对我在父亲督促下嗑嗑巴巴地讲南方的种种“妙处”已经不感兴趣,她连连责备父亲把两个女儿丢在南方,她为她们担心──母亲果真中计了。我想父亲此时在暗暗得意,他的“叶落归根”梦想可以实现了。
接着是迁徏南方一连串的准备工作,处理一些旧用具,办准迁证等。据说父亲在办退职手续时,遇到了麻烦,单位基于他的手受过工伤,不同意他退职。父亲又是苦苦要求,保证将来不以工伤来找单位,这样才得以批准。这些办妥之后,行李开始打包、托运,父母把炕桌、橱柜之类他们认为用得着的都带上。
那时的我,正处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忆,也不懂得操心未来的年纪。父母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。我只隐约觉得,某一天我还会回到这小镇来的──事实上,其后三十多年,我一直没有回到过大虎山小镇。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的一座小山,我家住过的老房子,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又是乘火车,坐轮船,我们全家到了安庆,稍事停留,就坐上一条木船去江南。这是一九六一年的早春,天气清冷,阴云凝结在空中,也许意识到重新开始生活的艰巨,父母望着江面,沉默无话。船在长江南岸停靠之后,水手们帮我们往下搬东西。天上开始掉雨点。
母亲走进不远处的沙地柳丛中,背对着我们坐下了。我看到母亲的身体在微微抖动,忍不住走过去。母系低垂着头,我看不见她的脸,只见到她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摔落在沙地上,和随风飘来的雨点混在了一道。后来,她站了起来,朝着北方看了好久好久。她的思乡之痛从此而开始,终生未能稍减。
艰难的日子
初来挖沟,我们借住在同一生产队的老鲍家,他家三间草房,让给我们一间。
老鲍是个看上去有些委琐的汉子,矮个,平顶头,肩膀有些病态地耸起。他有哮喘病,每到清早,喉咙里拉大锯,痰液呼呼响,整个身体像给谁抽了筋,佝偻成一团。太阳起山后,他才好一些,蹲到墙根,拿一把大烟袋一个劲喷云吐雾。他爱说笑话,常常吹嘘自己有过很多相好。初夏时,他到几十里外的开荒地去了,不常回家。
老鲍的婆娘长脸高颧骨,不认字也不识数,一双大脚,走起路来登登响。她不生育,抱养了一个病猫样的男孩,每天喂米汤。她从不收拾家务,鸡飞到灶台上去,猪则往厨房里乱窜。她对我们几个小孩倒怪欢喜的,但我们都躲开她。
家里分了七分自留地,父亲一发狠,全都种上小白菜,说这回饿不死了,青菜可以管饱。结果春季一到,白菜全都抽了苔子,地里开成黄花一片。这时依然没有什么粮食吃,天天吃菜为主,菜里顶多撒把糠,人们脸都吃绿了。
父母要参加生产队干活,他们从来没正经当过农民,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,每天都很累,但毕竟也干下来了。母亲除了地里干活,回家还要缝补洗涮,更辛苦些。
这段时间,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吃黄连粉,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这种黑粉,让母亲做饼给他吃,邻居们都说黄连苦得要命,是下不了口的。但父亲坚持要吃,他大口地吞咽这些黑粉,脸上努力不流露一丝苦意,显得十分悲壮,母亲却扭转身子哭了。
另一件事是父亲赤膊到地里干活,上身晒出了一层水泡,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,但他没叫一声痛。
紧接着到来的夏天对于母亲来说,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煎熬。先是梅雨季节,天天下雨,几乎在一个月内没出过太阳,气候潮湿闷热,母亲对此特别不习惯,身上整天都是汗淋淋的。
热呵,真热,母亲发出痛苦的叹息。她吃不下东西,晚上也睡不好,半夜里走来走去,想找个有风的地方。
梅雨过后,多日连晴,火毒的太阳从早到晚地照着,土地晒得烫脚,村庄沉浸在一股热浪中。母亲热得上不来气,垂弯着背,脸色青黄,昏昏沉沉地坐在背阴的地方。就这样,她还坚持给我们做饭,洗衣,还要到地里干活。
她对付热的唯一办法是往头上倒凉水。头发干了,再倒,总让头上水淋淋的。本地人都劝她歇歇,说身子要紧,不然出个三长两短,孩子们可怎么办。
母亲背着我们,不知流了多少眼泪,每一个白天和夜晚,她都是苦苦挨过的。甚至几年之后,在我们全家人都基本适应南方的酷热之后,母亲仍然极其害怕过夏天。
多年之后她对我说,当时实在不行了,好几次准备拎个包袱回东北,之所以没走成,最主要的是放心不下我们这些孩子。
在老鲍家住过一段时间以后,我们又搬到生产队的一处空房子里住,是一排四间房,中间用芦苇杆隔开,两家人住。隔壁住的是老马一家人,由于芦苇不隔音,两家人说话走路互相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老马是个老实巴脚的农民,脸膛很黑,言语特别少。他是从外地招亲来的,有力气,能苦做。
我还记得他女儿马兰花出生的事。是一天夜晚,老听到隔壁叽叽哝哝的有人说话,急促的脚步响个不停。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在说快了快了。一两个时辰以后,一声婴儿的啼哭吓了我一跳,才知道隔壁人家生小孩了。从那以后我知道,生小孩原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
这时候,荒年逐渐过去,粮食能勉强糊口了。大姐转学到安庆四中读书,二姐和我在离家不远的兴安小学上学。
不久,我们又第三次搬家,这次是搬到村西头的饲养场。
饲养场
一生中住过许多地方,“饲养场”我始终记忆犹深。
所谓饲养场,原是公社化时期大队里的养猪场,饥荒来临,猪养不下去了,就把房子给了村里的孤寡老人住。
我还记得姓江和姓丁的两位老太太,江老太身子瘦弱,脸上有些浮肿,衣服又脏又破,有点疯疯癲癫,喜欢唱着歌在场地上走来走去。她嗓音喑哑,老是唱一首老歌:“嘿啦啦啦,嘿啦啦,打败美国侉哟,遍地开红花呀──”
丁老太和江老太截然不同,她年纪大些,但身体很好,一双小脚走路重心却很稳。她不苟言笑,一天到晚驮着个竹筢子,筢子上再吊个篾篮,到树林里去筢树叶子。筢回的叶子在门口堆了很多,一年半载都烧不完,她还不肯歇歇腿。
江老太懒,总是没柴烧,就很忌妒丁老太,常在我们面前说她的坏话,如讲她阴坏,偷东西等等。讲的时候通红的眼角布满了眼屎。
我们家住的房子稍大些,屋后有一口水塘,塘边长满大树,绿森森的。又一个炎夏来临,家里没有凉床,每到黄昏,母亲先往大树下空地上泼凉水,去掉些暑气,然后让我们拆下门板,在风口搭起睡铺。那时父亲为队里值夜守庄稼,吃过晚饭出门,隔天早晨才归家。
我们睡在夜空下,心思随着星星远去,露水渐渐润湿了眼皮,于是飘渺的梦境来临。有些夜晚,风暴不期而至,母亲一个个推醒我们,怕惊着我们压低声音急促地说:孩子,快起来,要变天了。我睁眼看看天空,果然大块的黑云已经阴险地集结,沉沉欲坠。大风从田野的尽头嘶啸而来。
在一种半睡半醒状态中,我们赶紧拆除睡铺,把门抬回原处。这时风暴已经猛烈扫过我们的小屋,我们的头发和高高的大树同样翻卷起来。门板被风吹得把持不住,怎么也上不回门框里去。风凶险地灌入屋内,屋子开始在摇晃抖动。
母亲紧张得声音断断续续,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:天呵天呵老天呵。她的手臂既要抵住门板,又要照护我们,怕我们给风吹跑。终于门插进轴里,但却给风吹得拴不上,我们竭尽全力,通过薄薄的门,和凶恶的大风对峙着。风中的世界在抖动,我们的心也在抖动。
我们也经历过另外一种恐惧之夜。深夜,整个村庄都沉浸在睡梦中,突然有个人是说梦话还是因为某种神经质般的恐惧,惊呼一声:老虎来了!在露天沉睡着的人们全给惊醒,连忙不顾一切地往家跑。
没有人真看见过老虎,但也没有人不惊惶失措。这种骚乱有时要惊扰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,像炸了窝一样,由某个人梦中的一声尖叫开始,村庄里随之而起一片喧哗呼号的声浪,脚步乱纷纷的,有什么东西给碰得轰然一响。大人小孩猛然一齐发出驱赶巨兽的“唆唆”声。被黑夜分割的惊慌恐惧的人们,只有通过喊声相互壮胆。
白天时,人们谈起这事,觉得可笑,但一到晚上又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村人不由自主地随着丧魂落魄的村庄一起惊悚不止。这也可能是荒年之后日子虽然逐渐正常,但人们对灾祸仍余悸未消的缘故。
在这样的夜晚,母亲总是连拉带拽地让我们这些孩子回到家里,然后紧紧拴上大门,再把桌椅板凳搬过来顶住。她点上一盏油灯,我们几张惊魂未定、没有血色的脸就都依偎在灯影里。巨兽舔啮我们的神智;巨兽和夜色一样无所不在。
母亲隐在窗口,久久地朝外窥探。家里闷热异常,汗湿衣衫,但没有谁敢到外面去。黑夜早已没了动静,油灯却始终无人吹灭,直到黎明来临,灯油干了熄灭为止。
免责声明:本文为转载,非本网原创内容,不代表本网观点。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,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、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,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
-
易烊千玺夜景随拍 四字真是妥妥文艺男啊
【易烊千玺夜景随拍, 四字真是妥妥文艺男啊】20日,易烊千玺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夜景随拍照。四字确实是妥妥文艺男青年啊。[详细] -
2023年第一季度5部高分剧,《狂飙》排在第三,你追过哪几部?
第五部《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》 豆瓣:7 8 主演:张若昀、王阳 剧情点评:一开始感觉有点无聊,但是后续渐入佳境。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邓知县和帅家...[详细] -
原创舞台剧《魔域·亚特之光》首演 共赴“爱与和平”成长征途
舞台剧《魔域·亚特之光》剧组 张帆 摄 中新网北京8月19日电 (记者 应妮)全新原创舞台剧《魔域·亚特之光》19日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[详细] -
众多电影人江西庐山推荐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
中新网庐山8月21日电 (记者 吴鹏泉 姜涛)第三届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主题盛典20日晚在江西庐山举行,众多电影人在活动中推荐中国影史经 [详细] -
直击义乌疫情:病毒隐匿性更强 一县支援一镇保供
发布会现场。 金华发布 供图 (抗击新冠肺炎)直击义乌疫情:病毒隐匿性更强 一县支援一镇保供 中新网金华8月14日电 (记者 张斌)8 [详细]